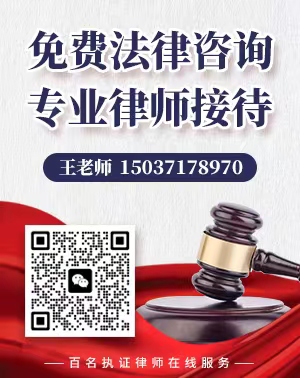京ICP備2022018928號-30 投訴舉報:315 541 185@qq.com
拾夢·追夢·圓夢——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一位戍邊老兵的“夢想圓舞曲”
在北疆邊防駐守27年的老兵,究竟什么樣?也許你很難想象,他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執著。從炊事員“轉行”成了通信兵,他總是使“蠻勁”,耗費成倍的時間學技術、練專業,是戰友眼中的“一根筋”。
他豁達。革新發明多次申報專利,上級想把他調入某部專門搞發明,他卻離不開邊防線。“徒弟”們說,班長習慣了烏拉泊的風,你看,他的笑容多清澈。
他對生活“走心”。邊防線上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景都刻在他的腦海。連隊的軍犬和軍馬,他都饒有興致地取了“昵稱”。送給遠方妻子的禮物——戍邊石,每一顆他都做了時間標記。營院外的銀杏林,從小苗長成參天大樹,望著陽光下生機盎然的綠葉,他會告訴新兵,熱愛你的生活吧。
他,叫許永濤,新疆軍區烏拉泊邊防連一級軍士長。到連隊那天,許永濤剛滿18歲。夜晚站在荒原上,他抬頭望天,璀璨星辰仿佛伸手可摘。這里,就是他站立的地方。環境的艱苦,賦予了他樂觀的性格;任務的艱辛,磨礪著他的意志品格;肩負的責任,讓他一次次懂得,清澈的愛,只為祖國。
老兵自有老兵的故事。今天就讓我們走近這位老兵的軍旅人生,并從他對生活的理解中,一起感受烏拉泊的勁風,領略山崗上那道美麗的青春彩虹!
——編 者
“你必須經歷失敗”
許永濤的軍旅記憶是由一個又一個攀登奮斗的“圓”組成的。
在那些伴著歡笑和淚水的記憶中,是一次次圓夢的經歷讓他有了一種感悟:“每次砥礪奮起都是在經歷挫折后,也是挫折讓人學會埋頭趕路。”
從拾夢、追夢,到圓夢,許永濤心里,這就像奮斗的路線閉環,只有堅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繪好自己生命的“圓”、夢想的“圓”。
假如青春是一個“圓”,你會如何揮舞手中的“畫筆”?
去年底的連隊政治教育課上,入伍近30年的許永濤走上講臺,作為全團最老的老兵,向臺下新戰友拋出這個問題。
在準備課程時,許永濤認真翻看了陪伴他近30年的記事本,昔日的得與失、收獲和失落躍然紙上,他不由得感慨:“經歷了失敗,才能奮起直追。走在一馬平川的大路上,難有跋山涉水的毅力。”這,也成為他授課講義中的“金句”:“你必須經歷失敗。”
第一次經歷失敗,是在許永濤高中畢業時。付出了努力,卻名落孫山,他滿腹懊惱和自責,“投筆從戎”的想法在那個冬天逐漸占據了他的腦海。
當時的陜西關中地區相對閉塞,父親送許永濤去部隊那天,他一路替兒子背著行李。咸陽火車站站臺上,面對從未出過遠門的許永濤,老人一把拭去淚水:“你離開家是去報效祖國,全家人為你驕傲。”
向西的列車里,擠滿一張張稚氣的面孔。聽著鐵軌撞擊的響聲,許永濤掂量著父親的話,反復咀嚼這些話的重量、琢磨話里話外的鼓勵與鞭策。奮斗之路,從這一刻開啟。
新訓結束,許永濤上了“訓練龍虎榜”,下連時,他被分配到離團部最遠的烏拉泊邊防連。“最優秀的新兵,才能來到最艱苦的連隊。”老兵告訴他,烏拉泊海拔雖不高,風卻大得讓人受不了。
守防數月,許永濤適應了哨所的風——風里做單杠練習,他能拿到優秀成績;風里巡邏,他用背包繩系在腰間與戰友保持隊形;哨樓執勤,他見過旗桿被旋風吹倒,也見過“風吹雪”時戰友被吹成了雪人;還有一次,他和戰友在宿舍剛睡下,一陣狂風掀翻了房頂,他們裹上大衣在風里“戰斗”到天亮……
然而,挫敗感來得猝不及防。
授銜儀式上,一心想進戰斗班排的他站得筆直,等來的卻是連長的命令:“許永濤,炊事班!”
“一個炊事員,能頂半個指導員。” 連隊干部這樣對他說。“不管在部隊干啥,咱都得干一行愛一行,踏踏實實為部隊作貢獻。”父親電話中這樣對他說。許永濤的思想也漸漸“轉過彎來”:無論是戰斗員還是炊事員,崗位就是戰位,揮舞鍋鏟也是為戰斗力“加油蓄能”;要想走出挫敗感的陰影,首先要把自己的戰位守好,把手中的“武藝”練精。
一個月時間,喂豬、擇菜、炒菜……炊事班的工作他逐漸得心應手,得到連隊官兵的一致贊揚。隨后的一次任務攻關中,許永濤被連隊臨時調整到通信兵的崗位上。
灶臺變成電臺,炊事車變成通信裝備車,許永濤同樣“干一行愛一行”。大半年時間,熄燈后,他打著手電筒在被窩琢磨學習。一次,營里組織崗位練兵,在裝備知識競賽環節,有位選手被隨機提問難住了,緊急求助觀眾。許永濤果斷回答,幫助戰友奪冠。
在那以后,許永濤的軍旅人生更加“開掛”:通信故障排除比賽,他名列前茅;“四會”教員比武,他成為唯一獲評優秀的士兵……他的努力,團領導看在眼里,一致決定:培養好這棵“苗子”。不久以后,許永濤正式成為一名通信兵。
堅持是成功的“秘訣”
一次參加編組聯訓,車載電臺只能“點對點”通信,實際任務卻要與多點位通聯。許永濤架起多副天線,如此一來節省了時間,但每次轉換天線時,他都要重新連接電路。
許永濤善于思考,坐在值勤機臺上,他突然迸發靈感:“假如有一套天線轉換裝置,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目標近在眼前,卻是一個大工程。那個冬天,烏拉泊平均氣溫低至-20℃,許永濤和技術人員每天在信息車廂一待就是大半天,設計圖紙,試驗論證,他的手上長出凍瘡。
一個月后,許永濤將天線控制轉換器設計方案上報領導,戰友有人贊賞,也有人質疑:“兵就是兵,何必操著領導的心?”方案呈到團領導的辦公桌上時,他看到了信任的目光。
設備試驗階段,許永濤反復與生產廠家電話溝通;采購元件,他跑遍了駐地的電子加工廠,向師傅學習板件焊接技巧。由于缺乏實際加工經驗,歷經3個月的探索,他還是失敗了。
通往成功的路上,不僅有鮮花。
那天夜里,許永濤夢見了母親。翌日一早,他就撥通了家中電話,沒想到迎面一道“晴天霹靂”:母親因腦出血去世了。
“不要告訴兒子。”這是母親在彌留之際,與父親的約定。
淚水涌出眼眶,許永濤跪倒在戈壁灘上,朝著家的方向,他向母親磕了三個頭。那夜星河燦爛,望著繁星點點,他的眼睛濕潤了,他知道,那是母親在望著他。
把悲傷藏在心底,許永濤重新回到攻關戰場。那段時間,他將自己關在車廂,日夜潛心研究,反復推倒重來,直至天線轉換器試驗成功,并在上級機關舉辦的創新評比中拿了獎。
拿到獎狀那天,許永濤睡了一個踏實覺。想起母親在他初入軍營時對他說的話:“不管天大的困難,一定要堅持。”
堅持,這是成功的一個“秘訣”。他的眼睛再一次濕潤了。
“我們的態度決定一切”
入伍的第二年秋天,班長帶著許永濤在營院外的荒地上種下一片銀杏林。
那時,樹苗只到他的腰那么高。
休息時間,班長和許永濤經常到銀杏林除草、澆水,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呵護樹苗。一次,班長望著這片陽光下的綠葉,若有所思地說:“我們怎樣看待生活,生活就會怎樣回饋我們。”
一眨眼5年過去了,老班長即將脫下軍裝。離別的人群中,目送那個熟悉的身影漸行漸遠,許永濤的淚水涌出眼眶。
歲月催熟草木。戰友離去后,許永濤再次來到銀杏林,當初的小樹,如今已經長成了十幾米的大樹,微風拂過,金黃的銀杏葉隨風起舞。他拾起一片,夾在筆記本里。
許永濤也漸漸成了別人眼中的“老班長”,面對初上戰位的年輕人,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當年的樣子。
架天線訓練,許永濤站在車頂操作,每一個拼接和固定的動作都經過成百上千次的“機械練習”,形成了標準的“肌肉記憶”。在指導新兵操作時,他會告訴大家,“標準是堅持下來的,我們的態度決定一切”。
嚴苛的帶教模式,讓許永濤帶出了一茬茬業務精兵。而在“徒弟”眼中,他們的“師傅”如父如兄,“許班長關心我們的生活,他告訴我們,對待生活首先要抱以熱情的態度”。
有一年高原駐訓,酷熱難當。許永濤帶著“徒弟”下士郭小勇頂著大太陽革新某型裝備。他中暑暈倒了2次,卻“命令”郭小勇翌日在宿舍休息。第二天天還沒亮,他就早早起了床,獨自一人開始了研究。
那年,中士張帥因為山上任務,推遲了婚期,許永濤悄悄把這件事寫在記事本上。轉過年來的春節前夕,連隊開展“云視頻”活動,許永濤悄悄聯系了張帥遠在武漢的妻子,錄了一段視頻表達心聲:“今年,我想要一場高原婚禮。”
如今,許永濤的記事本上已經寫滿了心愿。那本被歲月浸染得有些泛黃的本子,陪他踏遍雪山哨卡、穿越春秋冬夏,如同封存在大樹軀干里的一圈圈年輪,記錄下他和戰友們的青春歲月,記錄下他們誓守山河的承諾。
平平淡淡才是真
夜深了,雪停下來,邊境線的雪夜格外靜謐。每年初雪降落的日子,許永濤都會打個電話給遠方的妻子王艷。守防27年,這個和妻子的不成文的約定,他也堅持了27年。
兩人第一次書信聯系,是那一年第一場雪飄落的時候。
許永濤閱讀著娟秀的字跡,心里暖暖的。他的回信,卻是在第二年元旦假期寄出的。
大雪把上哨的路掩埋了整整兩個月,遠在西安上學的王艷,每天到傳達室看信,卻總悻悻而歸。那時邊防一線手機信號還未實現全覆蓋,兩人就因為一場雪斷了聯系。
“你還好嗎?”再次讀到信時,王艷已經放假回到咸陽老家。遠方的問候和信紙上的文字,一瞬間消融了兩人之間的誤會。王艷甚至覺得,是那場雪,讓他們的心長久向往,彼此牽系,再也不能分開。
在這對遠隔兩地27年的夫妻心中,總有一些特別的回憶,見證他們的感情。每到下雪的日子,王艷就會想起遠方的溫暖。也是一年又一年的守護,他們感受到了彼此的真摯情感。
多年過去,烏拉泊邊防連附近建好了移動基站,許永濤平靜地撥通了王艷的手機號碼,等待遠方那一聲熟悉的問候。
“終于可以每天通電話了”“別說通電話,每天視頻連線,那也沒啥問題”……在信息發展讓世界成為“地球村”的時代,分隔異地的夫妻倆,心心相守的夢想,再也不會輸給現實的距離。
在彼此牽掛的日子里,他們漸漸接受了距離,漸漸習慣了不能時刻團圓的守護,就像王艷說的那樣,生活就是這樣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才能到永遠。
在北疆守防的日子,許永濤經常給妻子尋找駐地的戈壁河灘石,用砂紙細細打磨后,每一塊都有精美的圖案。
穿越風雪的石頭,每一顆都被許永濤標注了時間。
“這顆是兒子出生時他撿的,那顆是他第一次探親回家時打磨的……”兩人安家在西安,精巧干凈的客廳里,一家人的合影幸福溫馨,客廳北面的書櫥中,王艷把丈夫寄來的石頭悉心珍藏。她說:“這是高原的禮物,也是愛的見證。”
此刻的邊防線上,寒風驟起。車窗外,一抹霞光緩緩躍出地平線。
收整行裝、啟動車輛,許永濤結束任務,與戰友一起向著連隊的方向駛去。
遠方的光那么溫暖。許永濤望著霞光,想著幾千公里外的妻兒應該已經回到家中,準備吃晚飯,他的臉上浮現幸福的笑容。
(薛 鵬 蒲杰鴻 王正陽 解放軍報)
 15037178970
15037178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