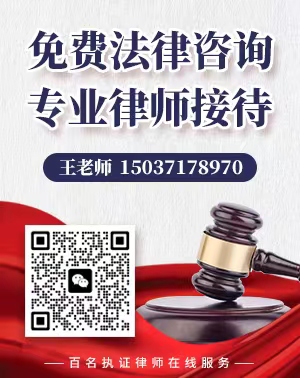京ICP備2022018928號-30 投訴舉報:315 541 185@qq.com
服裝設計是各大服裝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之一,可以為經營者帶來更多的競爭優勢,但其在司法實踐中卻很難獲得保護。除了通過《著作權法》《專利法》對服裝設計進行保護,《反不正當競爭法》在服裝設計保護方面也能提供獨特的維權途徑和價值。為此,筆者對相關判例進行了梳理與總結,以期對服裝行業的維權方式提供一些指引。
一、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大量抄襲服裝設計的行為進行規制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如果對方大量抄襲權利人的服裝設計,雖然單個服裝設計不能獲得法律的保護,但是這種大量抄襲的行為是否會因為量變產生“質變”,而應當受到法律的規制?
筆者認為,從本質上來看,這類行為與目前數據領域大量搬運、抄襲他人數據的情形類似,都是不勞而獲,直接使用他人資源,在市場中足以實質性替代他人產品,具有不正當性,構成不正當競爭。
從保護模式上來看,不正當競爭行為與知識產權侵權不同。知識產權侵權判斷模式都是權利侵害模式,即未經許可使用某類權利,且無免責事由的,構成侵權。這種侵權判斷模式通常先論述出一個受保護的權利,以此為出發點,并根據其受到損害而認定構成侵權。而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則適用行為譴責式的判斷模式。《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法益是民事利益,民事利益與絕對權利不同,缺乏公示性和排他性,因此,對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應著重通過對侵害行為正當性的評判,認定是否構成不正當競爭。對所涉利益的判斷,通常如果權利人的經營行為正當合法,其相應的經營成果,包括服裝設計樣式等,就可以獲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正是因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所保護權益的要求沒有著作權那么高,更注重對不正當性行為的規制,所以其對規制抄襲服裝設計類行為有獨特的優勢和價值。
在廣州愛帛服飾有限公司(下稱愛帛公司)訴杭州萊哲服飾有限公司(下稱萊哲公司)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1]中,廣州互聯網法院認定,被告萊哲公司銷售的99款服裝款式抄襲原告愛帛公司的服裝設計樣式,并抄襲了產品宣傳圖片和內容,當消費者通過“搜同款”功能看到被告的同款服裝和類似的宣傳介紹時,容易導致誤認原被告的同款服裝具有相同的質量保障,進而容易產生混淆。因此被告的行為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款“其他足以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混淆行為”。雖然對于被告的行為是應該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款還是第二條原則性條款存在一些爭議,但該判決中對被告行為具有不正當性以及對市場競爭秩序破壞的認定,對于同類案件有借鑒意義:
1.服裝經營者在追隨當季流行風尚時,為形成一個新的時尚潮流,離不開行業內各經營者爭相效仿流行元素,比如“格子”“豹紋”“拼接”等等,因此各自服裝產品難免存在相似之處。如果在兩個服裝經營者之間,僅僅三五件缺乏獨創性的衣服款式雷同,恐無法排除各自設計純屬巧合的可能,不足以認定為擅自使用。本案中,被告萊哲公司與原告愛帛公司在99件服裝款式上存在程度不一的相似性,其中部分款式幾乎完全一致,而且被告萊哲公司的部分宣傳內容、模特姿勢和服裝款式搭配等圖片背景與原告愛帛公司的產品相同或高度近似。在這種大面積相似的情況下,被告未證明所有款式均為其原創設計,經法院釋明及追問,被告亦未提供設計來源,故被告萊哲公司仿冒的款式來源于原告愛帛公司已達到高度蓋然性,主觀上構成擅自使用。
2.原告服裝品牌已經擁有獨特的風格,其款式在市場上擁有一定的辨識度和影響力。原告愛帛公司在國內擁有2000多家零售門店,粉絲數量巨大,產品銷售量大,因此原告旗下品牌服裝具有較高的知名度,而品牌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輻射到款式設計上,佐證涉案服裝款式的影響力。
3.被告萊哲公司的仿冒行為易導致部分消費者誤認為其同款衣服可能具有與原告基本相同的質量保障,提升對被告服裝的認可度。由于一款產品的售價主要是由生產成本、經營模式、品牌價值、市場需求等眾多因素決定,會有部分消費者認為原告同款服裝價格較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品牌溢價等,而雙方在服裝質量上實際相差不大,于是抱著試一試的僥幸心理購買被告的同款“廉價”服裝,期待能慧眼識珠“淘寶”成功。因此,當消費者通過“搜同款”功能搜尋到被告的同款服裝,又看到被告對服裝的宣傳介紹雷同時,更容易誤認原被告的同款衣服具有相同的質量保障,進而提升對被告服裝的認可度。
4.因為被告萊哲公司緊跟其后的抄襲行為,原告愛帛公司難以利用先發優勢彌補研發支出,同時因被告萊哲公司不用承擔設計成本,相比愛帛公司存在一定競爭優勢,更易在價格戰中勝出,進而攫取原告愛帛公司的整體商業優勢。因此,被告萊哲公司的此類搭便車行為會導致在先創新無法獲得合理的回報,這種“誰創新誰虧損”的現實局面將造成沒有經營者再愿意先行投入,大家迫于無奈都只能觀望和等待他人創新企圖“搭便車”,久而久之整個市場將處于止步不前的停滯狀態。
二、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對抄襲服裝設計、款號/貨號、吊牌等行為進行規制
這類行為與第二類大量抄襲服裝設計樣式的區別在于,其抄襲服裝設計樣式的數量不構成大量,但是同時抄襲了權利人的服裝款號/貨號、吊牌等,也即有多種不同的抄襲行為。這類行為與第二類行為本質類似,被告主觀有搭便車的故意,通過不誠信、不正當的行為攀附了原告的商譽,對原告所具有的法律上值得保護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損害,構成法律所禁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規制。
服裝貨號,也稱為“款號”,是服裝企業編制的商品標識代碼,該代碼具有唯一性,每一款服裝產品都有一個全球唯一的編碼。服裝貨號的目的是使服裝商品條碼在滿足超市結算需要的同時,又能滿足企業內部產品信息管理的需要。貨號編碼規則由一串數字和字母構成,通常包含具體產品的品牌、上市年份、月份、細分品類、流水號、貨品屬性、色號等[2]。服裝款號不僅是生產廠商和銷售方管理商品的編號,同時也是消費者通過檢索款號定位到自己需求的服裝的重要途徑。目前不少服裝品牌在商品銷售標題上直接表明服裝貨號,比如Nike、H&M、Gloria、ONLY等。
除了直接抄襲服裝設計樣式,目前還出現了抄襲他人服裝款號、貨號,謀取非法獲利的情形。服裝的款號、貨號雖不屬于受知識產權專門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保護的客體,但如果使用他人服裝款號、貨號的行為違反商業道德,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可直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予以規制。
在杭州江南布衣服飾有限公司(下稱江南布衣公司)訴姜建飛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3]中,被告姜建飛銷售46款與江南布衣公司相同款式的服裝并使用相同服裝款號。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再審審理中認定:
1.款號主要起到吸引網絡用戶流量的作用,相關公眾可以據此搜索到與江南布衣公司款式相同的姜建飛的服飾,受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保護;
2.被告在不付出任何創造性勞動的情況下,大規模照搬照抄江南布衣公司的服裝款式并輔以相關款號引流,并在其商品鏈接名稱等處標明“江南布衣風”,主觀上有攀附的惡意;
3.被告的行為明顯擠占了江南布衣公司的交易機會,已經對江南布衣公司的商品構成實質性替代,給江南布衣公司造成實質損害。特別是江南布衣公司所處的時尚流行服飾行業屬于快速消費品行業,產品生命周期較短,相關服裝款式和款號一旦被快速大規模仿冒,會對產品設計、生產企業的利益造成極大損害。從消費者利益角度看,相關消費者雖然在短時間內能買到更便宜的流行服飾,但如果對此類大規模仿冒行為不予規制,必然導致原創設計動力衰退,長期來看并不利于消費者利益。
類似的,在綾致時裝(天津)有限公司(下稱綾致公司)訴被告博野縣幻蝶霧語服裝店(下稱幻蝶霧語服裝店)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案件[4]中,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二審中認定被告幻蝶霧語服裝店“在相同或類似的款式上使用與綾致公司相同的款號,將通過款號搜索綾致公司服裝的消費者引流到其店鋪,購買其銷售的類似款式的服裝,以獲取不正當的競爭優勢。該行為明顯擠占了綾致公司的交易機會,已經對綾致公司的商品構成實質性的替代”,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構成不正當競爭。
在江南布衣案和綾致公司案件中,法院均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原則性條款,是因為原告未提供充足的證據證明涉案服裝款式、貨號具有很高知名度,無法適用具體的條款進行規制。如果原告能夠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受保護的權益,包括涉案服裝款式、貨號具有較高知名度,還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款“其他足以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混淆行為”。在原告南京圣迪奧時裝有限公司訴被告劉世琴、穆妮妮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5]中,南京中院不僅將9個專利案一并審理,還認定“貨號和服裝款式之間具有對應關系,消費者在購買相關商品的過程中往往以貨號作為關鍵信息進行檢索”,劉世琴、穆妮妮在被訴侵權商品上使用與圣迪奧公司相同的服裝貨號,并使用與原告同款服裝相同的吊牌價和成份等標識信息,目的是為了引導消費者通過貨號檢索到其所銷售的產品,獲取不正當的競爭優勢,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款的規定,構成不正當競爭。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視角下服裝設計司法保護的總結
從目前司法實踐來看,如果服裝設計本身設計感不強,但是侵權人抄襲的惡意非常明顯,比如抄襲了權利人大量的服裝設計樣式、抄襲了權利人的多種服裝款式內容,包括服裝設計樣式、服裝貨號、服裝吊牌等,則可以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或第六條第四款予以規制。而究竟適用哪條法律,不同法院尚有不同見解。如果服裝的款式款號通過大量的宣傳和銷售具有較高知名度,已經與權利人構成一一對應的關系,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下應該優先適《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款“其他混淆行為”,相反如果不能證明具有較高知名度,則需要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原則性條款。
與此同時,服裝企業在進行維權的時候,也要注意維權方式的合理性,防止因不當維權方式引發侵權風險并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比如向涉嫌侵權人發送律師函的時候需謹慎,尤其在侵權與否尚未有明確定論的時候,不要使用絕對化、誤導性措辭,也不能對事實僅做片面描述,也不宜直接將律師函、溝通函通過社交媒體對外公布或發送給涉嫌侵權人的合作伙伴,這種傳播和影響范圍很可能會被認定已經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涉嫌構成商業詆毀的不正當競爭。
注釋
[1](2021)粵0192民初11888號判決書.
[2](2022)浙民再256號判決書.
[3](2022)浙民再256號民事判決書.
[4](2021)冀知民終294號民事判決書.
[5](2019)蘇01民初728號民事判決書.
 15037178970
15037178970